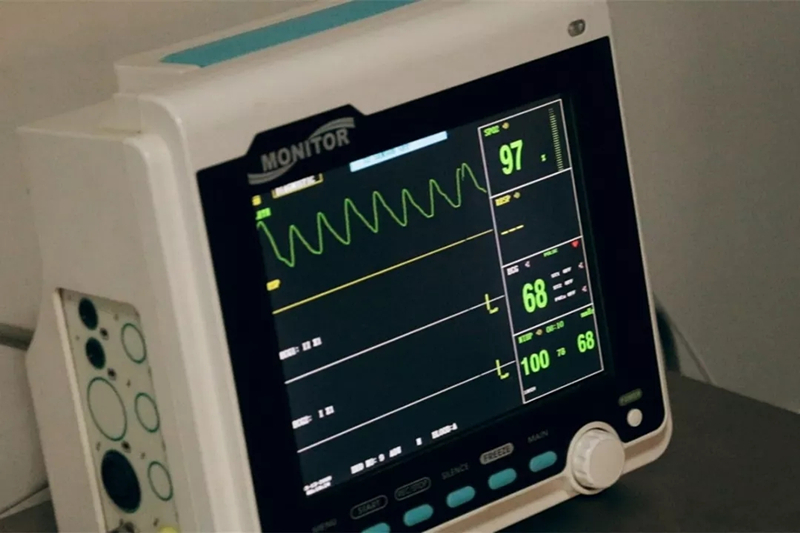清明副刊:左手敬礼的金永继

前年秋天去西宁出差,听西宁的战友不经意提起“金永继没了”,我才知道当年那个跟我一起受苦受难的兄弟已经悄然离开人世。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记得他,但对于他的遭遇却没帮上任何忙。谨以此文纪念战友金永继。
第一次见金永继,是在新兵连的时候。
我还记得,那天我是连值日,守在门岗上,一名班长带着一排右手持小凳的新兵走了过来,我起立,向他们敬礼。其中个子最高的一个新兵,慌乱中,用左手向我回礼。哗的一下,大家都笑了。班长也笑骂:黏糊蛋!
用左手敬礼?
敬礼用右手,这是全世界军人通行的规则。按照当时的条例规定,带队班长可向我还礼,队伍中的其他新兵只须向我注视即可。但是这个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大个子,竟然用左手向我还礼,你说我能记不住他吗?
他就是金永继。
一个来自青海的农村兵,满脸的惶恐,这就是金永继留给我最初的印象。
新兵训练结束后,我和金永继分到了同一个老兵连。作为同年兵,我们的交流稍稍多了一些。但我们不在一个排,专业不一样,所以还不算很熟。
我和金永继真正熟悉起来,缘于我们共同遭遇的那场车祸。
我永远不会忘记,一九九四年的三月,某天傍晚,我们从国防施工工地上返回,已经从古浪的山路上回到了山下的平路,眼看就要到临时驻地了,军用卡车突然之间就翻车了。醒来后,我发现自己躺在公路上,一摸,满脸是血,嘴一张,吐出的仍然是血,大口的鲜血。战友们手忙脚乱,有人来抬我,有人拦车,有人跟我说话,怕我眼一闭就再也醒不来了。
战友们拦到了一辆兰州军区的首长专用吉普车,车上的首长一看,是部队军车出了车祸,立刻让我们上车,也不管是不是超载(前排是首长和司机,后排是三名伤员加上刘姓代理指导员)。然后司机加大马力,全力冲向位于武威的陆军第十医院。
就在这过程中,首长问清楚了事情的原委。而我在不断吐血的过程中,也迷迷糊糊地听了个大概。原来,当我们的军用卡车驶出古浪的山路后,带车干部,即刘指导员,擅自与司机交换座位,由他这个刚拿驾照不久的新手来开,在不断超车的过程中,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大拖拉机,刘指导员这个新手,猛打方向盘,结果让我们的军用卡车翻在了平路上。
事后我和金永继谈起出车祸的瞬间,他是一点都不清楚了,他只记得自己坐在车厢里打盹,车厢里乱作一团,不知道是撞的,还是被人压的,反正稀里糊涂地就把肩关节摔断了。
而我本人,眼看就要到临时驻地了,当时正好站起来观察,卡车侧翻的瞬间,我从车厢中直接飞了出去,像一块饼一样拍在了路面上。
非常幸运,在飞出去拍在路面上这仅仅一两秒钟的瞬间,已经失去意识的我,因为多年习武的本能保护,在接触地面的一刹那,是前扑姿势加侧脸着地。所以摔得满脸开花的我,并无大碍,陆军第十医院的医生检查完之后,非常欣喜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。
如果是以其他姿势着地,我可能早在刚刚年满二十岁时就告别人世了,而不是深夜里站在陆军第十医院的走廊上顾镜自怜,哀叹自己毁容了。
这一次车祸,除了我和金永继外,还有两名轻伤员,至于擦伤的战友,就没有列入统计了。
车祸完全是刘指导员的责任,他受到了降衔处分,并且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。
几天后,见我的伤势渐渐好转,刘指导员交待我照顾金永继,另一名同时住院的轻伤战友和他一起返回临时驻地。
那些天里,同病房的还有一个来自黄羊镇的老汉,家里卖了几千斤麦子送他来治病。我和金永继,还有老汉的儿子,没事就聊天。病房的窗外,正是春天的大好时光,杏树已经开花了。
我在医院里待得不耐烦了,于是主动申请回去施工,留下已经可以自行打饭的金永继继续住院治疗。
施工结束后,回到连队,金永继也出院了,左胳膊吊着纱带,左侧的肩胛骨高高翘起。他还要再做几次手术。
因为身体原因,金永继不能待在战斗班排了,左手永远蜷曲着的他被调去蔬菜班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
此后,我见到他时,他脸上的笑容,在我看来,怎么看都像是一种凄凉。
刘指导员是一个很有活动能力的人,在受到降衔处分后,他仍然担任连队的代理指导员,后来他军衔又晋升了,成了正式的指导员,再后来又转任了连长。
我在连队待了一年,后来想方设法调离了,根本原因就是无论我怎么努力说服自己,内心底还是非常反感刘指导员。而刘指导员这个人,我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形容他,反正在他手下服役,我可以用“如履薄冰”来形容日子的难熬。
事实证明,我调离原来的连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我在其他单位服役,尽管同样条件艰苦,但内心却非常快乐。工作之余,我和战友们共同组织了一支战士足球队,并且恢复了写作的习惯,在甘肃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,还和单位领导共同创办了一份战士刊物。而这一阶段的尝试,又为我此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反过来,一直待在原连队的金永继就没这么幸运了,服役满三年他就退伍回家了。在他退伍之前,我问他“残疾军人症”办好了没有。这是当初刘指导员答应他的事情。有了“残疾军人证”,金永继回乡后,生活多少有些保障。他非常难过地告诉我,没办下来。
我们当初同一个新兵连出来的战友,都鼓动他,去找刘指导员,不,现在的刘连长。
但是,直到金永继离开部队那天,他都没拿到“残疾军人证”。他就那样蜷曲着左手离开了部队。
两年后,我也离开了部队。
此后的日子里,我一直混在广东,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努力着。日常洗漱时,看着镜子中,自己脸上那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痕,我会想起曾经共同受苦受难的金永继。
那时,我们没有手机,甚至没有座机,更没有现在的QQ、微信,无法联系彼此。
当然,如果一定要找,我肯定能找到金永继的。可是,即使找上门去,我能说什么呢,我又能做什么呢?那时我不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“南漂”而已。
金永继是青海省民和县人,对于他退役后的日子,我一概不知,直到2018年,我到西宁出差,与当初同连队的两个家住西宁的战友碰面,一个战友告诉我金永继“没了”。
据那位战友转述的民和县的另外一位战友的话,说金永继大约在二零零二年、二零零三年时就因病去世了,所患疾病不知道是肺癌还是胃癌,反正是不治之症。在贫困的青海农村,比一般人更贫困的金永继,显然无法支撑下去。还说,这是民和县那位战友,偶遇金永继的哥哥,才得知的情况。
刹那间,我的眼泪出来了。
我怎么也想不到,当年在部队一别,竟然就是永别。用左手敬礼的战友金永继,脸上带着凄凉笑意的金永继,我再也见不到了。